宣德元年(1426年)八月月吉开云「中国」Kaiyun官网登录入口,汉王朱高煦终于耐不住寥寂,在藩国乐安州(今山东惠民县)起兵造大侄子的反。身处嫌疑之地确当世第别称将英国公张辅,在洗脱嫌疑之后,第一本事奏请领兵平叛。可汉王在当年乃屡次救太宗于生灵涂炭的靖难功臣,明宣宗想虑再三否决这一央求,决定御驾亲征,以免重蹈当年建文君的覆辙。 紫禁城文渊阁 皇帝领军在外,京城的抚慰尤为要害。此时皇帝尚无子嗣,只可从在京诸弟中挑选监国东说念主选。最终老五襄王朱瞻墡胜出,跳动胞兄越王朱瞻墉,与庶兄郑王朱瞻埈一齐...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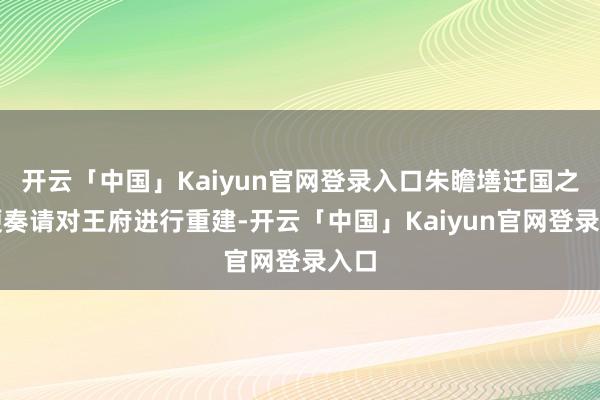
宣德元年(1426年)八月月吉开云「中国」Kaiyun官网登录入口,汉王朱高煦终于耐不住寥寂,在藩国乐安州(今山东惠民县)起兵造大侄子的反。身处嫌疑之地确当世第别称将英国公张辅,在洗脱嫌疑之后,第一本事奏请领兵平叛。可汉王在当年乃屡次救太宗于生灵涂炭的靖难功臣,明宣宗想虑再三否决这一央求,决定御驾亲征,以免重蹈当年建文君的覆辙。
紫禁城文渊阁

皇帝领军在外,京城的抚慰尤为要害。此时皇帝尚无子嗣,只可从在京诸弟中挑选监国东说念主选。最终老五襄王朱瞻墡胜出,跳动胞兄越王朱瞻墉,与庶兄郑王朱瞻埈一齐罢免居守北京,总理诸官。同期,明宣宗还命姑父广平侯袁容、靖难功臣武安侯郑亨等文武诸臣协助。
襄王朱瞻墡究竟是多么东说念主物,为何得以高出胞兄,与庶兄共同监国?他的身上又有哪些精彩故事呢?
第一次与皇位擦肩而过
朱瞻墡(音shàn),生于永乐四年(1406年)三月十六日,为明仁宗朱高炽的嫡五子,生母诚孝昭皇后张氏。与明宣宗朱瞻基、越王朱瞻墉为一母本族,乃明仁宗三个嫡子中的最幼者。
永乐朝,因皇祖父与父王之间精巧的关系,除被祖父切身供养的皇太孙朱瞻基外,朱瞻墡昆玉齐莫得被授爵。直到永乐二十二年(1424年)七月,明成祖朱棣病逝于归师途中,皇太子朱高炽继位,才迎来蜕变。当年十月,明仁宗大封宗室,19岁的朱瞻墡被册为襄王。
《明史》对朱瞻墡的评价为“庄警有令誉”,故在父皇逝世后,一度成为大兄明宣宗朱瞻基的牛逼襄理。汉王之乱时罢免监国只是其一。
洪熙元年(1425年)九月,明仁宗梓宫发引,即送往天寿山陵区安葬,朱瞻墡罢免送父皇最后一程,并代行联系礼节。
宣德二年(1427年)十月初六,以太师、英国公张辅为正使,行在礼部尚书胡濙为副使,持节册东城戎马劝诱靖安之女为襄王妃。
结婚意味着离就藩之期不远。
衢州南孔家庙

细说起来,襄王的封国极端成心想。明前期亲王封号或源于古国,或源于州郡名,“襄”赫然与襄阳府唇一火齿寒,照理来说即便不分封于此,也会分封于邻近(至少是本省)。可宣德四年(1429年)二月,明宣宗命行在工部修建襄王等五王王府时,明确提到襄王府建于浙江衢州,也就是说衢州府才是其真确的封地。
“癸未……命行在工部遣官,往凤翔、衢州、建昌、韶州、安陆州,修治郑、襄、荆、淮、梁五王府。上谕之曰:‘诸王将之国,未有府第。其视所在卫所州治,不错为王居者,令军卫有司合力修理,务在完固,毋花费东说念主力。’”(《明宣宗实录》)
然则当年五月,皇帝陛下倏得改变主意,下令停建衢州襄王府,改以位于湖广长沙的旧谷王府为基础,兴建新的襄王府。
进击将朱瞻墡此衢州外迁,情理推测与当年明太祖改封嫡五子吴王朱橚为周王,封国由杭州改为河南开封疏导。浙江紧邻南直隶,又是税赋重地,历来为朝廷中枢之地,极力于侧目在此封爵藩王。故天然明仁宗给这位季子选了个好去向,胞兄在位后也没作念更动,可终末如故采取了改封。
五月十三日下诏对襄王进行改封,十四日礼部“条具合行事宜以闻”,意味着诸王之国近在刻下,再觅他出从零运行兴建襄王府赫然已来不足,是以长沙虽非善地,先后有两位藩王在此折戟千里沙,可有谷王府这个基础在,修缮起来更浅陋,是以也就只可让襄王殿下拼凑一下了。
当年七月,明宣宗不顾户部的看法,下诏赐与诸王岁禄一万石。八月初三,朱瞻墡五昆玉风雅辞陛之国,走古代版高速公路——京杭大运河南下的四王,路子南京时,还将停靠祭祀孝陵。
因襄王府改建工程上马本事太过仓促,以至于成为烂尾工程,王府主体虽得以修缮一新,可位于王府前边的左庙右社兴建却一拖再拖。
朱瞻墡为襄藩始封君,宗庙尚可缓一缓,但右社所在的社稷山川坛,乃祭祀本国社稷山川之所,属于重中之重,恶果襄王就藩经年都没能完工。宣德七年(1432年)二月,磨牙凿齿的襄藩长史司上奏朝廷,淡薄使用潭府旧坛见礼。
“癸卯,襄府长史司奏:‘本府未建社稷山川坛场,请于潭府旧坛行事。’上曰:‘坛场虽旧,苟致其洁清而将之以诚,神必享之。’命礼部如其请。”(《明宣宗实录》)
长沙得名地:白沙古井

无论如何,朱瞻墡在长沙安堵了下来,可紧随而来的年老驾崩又给他带来了一点转化。
宣德十年正月初三,明宣宗朱瞻基倏得病逝,常年37岁。其死后留住留个两个季子,年长的皇太子朱祁镇也才年仅9岁,定然无法胜任皇帝的日常责任。
也正因此,宫中坐窝传出拥立襄王的传言。皇帝驾崩,皇后孙氏得天独厚,太子不足以掌事,此时宫中真确的话事东说念主为明仁宗皇后、明宣宗与朱瞻墡的生母、皇太后张氏。一边是年幼的大孙子,一边是以贤著称的季子,立长也更能让仁宣之治持续下去,就内心而言张太后极有可能会有这种主见。是以所谓的“宫中”指谁了然于目。
可关于朝臣而言,这个传言极其可怕。襄王虽素来称贤,执政中也领有不少拥趸,可这是建立在他看成藩王的基础之上。但立襄王为帝,一来不安妥嫡宗子剿袭制,二来置皇太子于何地?要知说念宋太祖、宋太宗昆玉的殷鉴为时未远。
眼睁睁地看着先帝的法统就此拒绝,给皇位剿袭埋下隐患(此时朱瞻墡的胞兄越王朱瞻墉尚在),天然不是朝臣们所能接收的。
鉴于朝野的反对声浪,张太后不得不将重臣们召到乾清宫,指着身边的皇太子朱祁镇说这即是新皇帝,东说念主心才得以清闲。
“宣宗崩,英宗方九岁,宫中讹言将召立襄王矣。太后趣召诸大臣至乾清宫,指太子泣曰:‘此新皇帝也。’君臣呼万岁,滥调乃息。”(《明史·诚孝皇后传》)
迁国襄阳
远在湖广长沙的朱瞻墡很可能并不清醒有那么一刻,我方立皇位是那么的近。要是贯通此事,内心推测若干会有些海潮吧。
无论若何,大兄倏得龙御上宾,年幼的大侄子继位,母后执掌大权,看成受宠的嫡季子,不失为一大利好。
张太后在白首东说念主送黑发东说念主的打击下,未免会给小男儿多一份贵重之心。她虽以“毋坏祖先法”为由,断绝了朝臣们请她垂帘听政的建议,可并未放权。惟有朝廷松终结指缝,就够襄王殿下吃饱了。
太皇太后张氏剧照

比如王府校尉的禄粮按照门径为每月五斗,可大侄子继位后,朱瞻墡对此淡薄异议。奏称在京时本府校尉军东说念主每月支取实质粮一石,随其之国后反而减半,以至于连吃饭都成了问题,央求朝廷赐与增给。最终在行在户部的建议下,增给三斗。
再比如宣德十年十一月,襄王奏称本府乐师东说念主手不足,以至于每逢“理睬诏敕、进贺表笺”等大事时,清寒东说念主手。明英宗闻讯命行在礼部从南京教坊司抽掉乐师二十余户,交给襄王府使用。
这些都是末节,对朱瞻墡而言,皇位递次取得的最大自制即是逃离长沙。
长沙在秦汉及昔时被视为瘴疠之地,秦末义军魁首之一的吴芮被汉太祖刘邦封为长沙王,恶果成为汉初八位异姓王中唯独一个得以善终,且传承五世之东说念主。汉景帝时期,又将最不受宠皇子刘发分封到用功卑湿的长沙。
及至大明,天然潇湘一带早已开导训导,可彼时的长沙对大明宗室而言,亦非善地,先后有两位藩王折损于此。首封于此的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八子潭王朱梓,他于洪武十八年(1385年)之国长沙,二十三年(1390年)自焚于王府,不仅一代而一火,连个谥号都没取得。接着十九弟谷王朱穗于三十五年(公元1402年)十月自宣府改封至此,然则永乐十五年(1417年)因谋反被废为庶东说念主。
前文说过,襄王属于临时改封长沙,且因本事问题,王府久久没能完全落成,要说他莫得迁国的意愿那是竣工弗成能的。可限于年老的威严迟迟莫得步履。
待年老在世,大侄子继位,母后掌权,朱瞻墡的心想顿时活跃了起来。熬过明宣宗小祥,便迫不足待地奏请迁国,情理为“长沙卑湿,愿移亢爽地”。祖母尚在,明英宗天然不会为难这位亲叔叔,当即命有司于襄阳度地为建王府,并修社稷、山川、祠宇。
正宗元年(1436年)七月,襄王殿下风雅迁国襄阳府,至此终于名实相称。只是此次迁国依然有些仓促,以至于以襄阳卫署为基础底细兴建的襄阳襄王府规制有些错落,建筑洒落各处,不联贯属,难以驻防。
襄阳襄王府

也正因此,朱瞻墡迁国之初便奏请对王府进行重建。明英宗命湖广三司勘探,方位天然不敢苛待,实地勘核后画图上呈。恶果工部炸锅了,行在工部尚书吴中暗示如完全按照图纸施工,需调集上万民夫工匠耗尽三年本事方可完工。明英宗(实则应当是太皇太后)被这一工程量吓到了,下旨完毕此议,只对现有襄王府进行更正。
要说重建襄王府勘探期间,朱瞻墡莫得参与其中阿越是毫不屈气的。只可说,此时此刻的襄王殿下若干有点飘了。事实亦然如斯。
正宗初年,襄藩长史芮善,年老体弱,向朱瞻墡淡薄致政,也即退休。王府长史虽属于王府官,可毕竟是朝廷命官,退休需吏部批复方可。襄王殿下倒好,不经奏报自行派东说念主安排船只送回其乡。
以为泰斗受到寻衅的行在吏部,当即奏请治芮善及长史司仕宦行恶之罪。恶果明英宗以“恐有伤亲亲之谊”为由,赐与包涵。
“上恐有伤亲亲之谊,特宥之。且以书报王曰:‘朕惟叔之颖悟贤人,必不差失至此,虑为下东说念主玷污,故违祖先圭表。特令长史司仕宦从实回奏,芮善令致仕不问。’”(《明英宗实录》)
正宗四年(1439年)正月和闰二月,就在襄王府修缮之际,府内接连被盗。没能抓到盗贼的朱瞻墡,怒弗成遏地将心计全部流泻到了肩负守卫职责的王府侍卫头上,一不舒坦就把侍卫拎出来鞭打一顿。
王府仪卫正金聚等东说念主因此心胸怨怼,向湖广三司密告襄王行恶之事多达十四件。尤为致命的一条为:万寿圣节本日,令内使施兴、女户徐亮拜焚表章,并呼羽士萧说念真扶乩,所得内容有“天数玄玄,妙弗成言”等语。意即天命在襄王,他与龙椅有缘。
要道时刻,因捕盗不利而遭襄王毁谤的襄阳卫劝诱同知汤震又上树拔梯,奏称王府校尉手执器械,于夜深时期在城表里擒捕行东说念主检讨,搞得东说念主心惶惑,不知想干嘛。此举一朝查实等合谋反。
好在此时太皇太后张氏在位,天然迁徙了锦衣卫,可皇帝以“特念亲亲”为由,只逮捕了施兴等东说念主便将此事轻轻揭过,朱瞻墡本东说念主只受到“以书戒谕”的刑事背负。
经此敲打,朱瞻墡终于幡然改悔,规复贤王实质。
第二次与皇位擦肩而过
自明宣宗慎重汉王之乱后,藩王朝觐轨制名存实一火,即便贵为当朝皇帝的胞弟都概莫能免。比如宣德七年(1432年)十二月,远在长沙的朱瞻墡奏请朝觐,明宣宗先是夸赞其“恭爱之意”,接着暗示只让他一东说念主赴京,其他昆玉会若何想,是以让他等等再说,这一等即是十年,连龙椅都换了主东说念主,都没能成行。
明英宗剧照

直到正宗七年(1442年)十月,太皇太后张氏病危,绸缪于榻的她想子心切,明英宗这才下诏命在外的襄、郑、荆、淮四王(梁王逝世于上年)回京侍亲。
当年十二月十九日,朱瞻墡抵京,百官罢免赴奉天门东廊下参谒。不外这趟赴京的性质已发生改变,当年十月十八日太皇太后张氏崩,故由侍亲变为奔丧。
诚孝昭皇后张氏的在世,让少年心性的明英宗失了料理,而后信用大伴王振,执政堂之上和文吏们斗得不亦乐乎。
在王振“右武”倡议下,明英宗愈发千里醉武功,想要作念一个如同父皇、皇曾祖那般,上可安六合,下能治国的英主。
正宗十四年(1449年)七月,一同蒙古诸部的瓦剌太师也先率众犯境。明英宗闻讯喜形于色,我方师法先皇威风的契机终于来了,仓猝起兵御驾亲征。未成想八月十五那天,在土木堡化身瓦剌东说念主餐桌上的月饼。大明精锐扫地俱尽,大都朝廷重臣死于横死不说,其本东说念主也沦为也先的战利品,进而荣获“瓦剌留学生”、“叫门皇帝”等“敬称”。
皇帝被俘,瓦剌雄兵一步步靠拢京师,如何凝华东说念主心及是否南迁暂避矛头,成为摆在明英宗生母、皇太后孙氏和文武百官眼前,臻待惩处的要道问题。而这一切的前提是,得有东说念主站出来主办大局。
明英宗此时有三个男儿,可宗子朱见深年仅两岁,次子朱见清(即朱见潾)尚不足一岁半,第三子朱见湜更是刚刚朔月。若在无边里,拥立幼主也无弗成,但值此命悬一线之际,赫然极端不对适。
明英宗唯独的弟弟郕王朱祁钰,时年22岁,为唯独在京的成年亲王,安妥浊世立长的需求。可郕王殿下,既莫得任何政事训诫,也无其他让东说念主刻下一亮的进展,能否担起这一重负犹未可知。
有鉴于此,孙太后预见了远在长沙的小叔子:襄王朱瞻墡,筹议让他来主办大局。
“诸王中,瞻墡最长且贤,众望颇属。太后命取襄国金符入宫,不果召。瞻墡上书,请立皇宗子,令郕王监国,募勇智士迎车驾。”(《明史·诸王传》)
孙太后如斯采取也有我方的考量。
孙太后剧照

朱瞻墡时年44岁,年富力强,当年汉王之乱时曾罢免留守北京,有着处理政务的训诫和材干。且他又是仁庙的嫡子、宣庙的胞弟,身份上也合适。关于危难关头国赖长君的大明朝来说,竟然是弗成多得的合适东说念主选。
更要道的是,让郕王监国,一朝度过危境,足以让他取得庞高声望,一正一负间对我方男儿的皇位组成要害恐吓。而让襄王赴京监国,一来路线远处,极有可能尚未到任,一火国危境便得以摈斥,无需再让他监国,二来再若何样,身份毕竟隔了一重,对自家好大儿、对几个小孙孙的恐吓性无疑更小。
两相其害取其轻,这少量孙太后如故懂的。
但远水不解近渴,决定死保京师的朝臣更需要一位近在刻下的领袖,而非海北天南的虚君,何况皇帝出征时已命郕王留镇京师,由他监国严容庄容。为已毕这一筹议,文吏集团不吝执政堂之上演出全武行,对王振的马仔锦衣卫劝诱使马顺群起而殴之,拳拳到肉将其活生生打死。
在文吏们的抑止下,孙太后不得不一步步谢却,先是于八月十八日命郕王监国,后于九月初六立朱祁钰为帝,遥尊被俘的明英宗为太上皇,换取册立朱见深为皇太子。
朱瞻墡一方面深明事有缓急,一方面也不肯意趟这蹚污水,因此上疏请立朱见深为帝,令郕王监国,以为两全。恶果奏疏抵京时,朱祁钰早已坐上皇位。这就尴尬了,我方非但是皇帝新皇仍是的竞争者,还后知后觉的站错了队。
也正因此,参加景泰朝后,朱瞻墡时常向朝廷讨取诸如竹帛、古琴即野外等犒赏,以证心迹。明代宗也对此心照不宣,赐与恢复。更狠的是,他竟预选襄阳府城以西的五朵山为我方寿藏所在,报请朝廷批准后运行兴建,并屡次赶赴捕快。
“(景泰四年四月)丙申……先是,襄王瞻墡欲营寿藏于封内五朵山,奏乞听其预栽松柏,令军余防守,待四方宁谧之时修造。户部请移文勘实。至是湖广都布按三司官覆奏:此山与军民田土俱无联系。诏从王所请。”(《明英宗实录·废帝郕戾王附录》)
取得护卫军
景泰八年(1457年)正月,南宫之主、太上皇朱祁镇趁弟弟明代宗朱祁钰病重之机,在石亨等东说念主的协助下发动政变,见效夺回皇位。
公道而言,明代宗是一位好皇帝,唯独作念错的事,即是坐稳皇位后不顾仍是的商定,废了侄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,改立男儿朱见济为太子。本想让我方这一脉万世一系,可惜天不遂东说念主愿,朱见济只是当了一年的太子便短折了,导致邦本空悬。而这也给了朱祁镇落井下石的契机。
夺门之变

大侄子复辟,身为皇叔的朱瞻墡迎来了又一个东说念主生危境。
明宣宗龙御上宾后的立长传言,本就让明英宗对襄皇叔多有猜疑。明代宗病重之时,因其独子怀献太子朱见济早已逝世,剿袭东说念主问题成为朝臣们最为关注的中枢问题之一,并为此分红两大派。
一片认为应当立前皇太子、现沂王朱见深为皇太子,算是拨乱归正,背叛前议。然则给大明带来沉重晦气的太上皇依然在世,父为子纲,此举难保他不会出来作妖。故另一片筹议从根子上摈斥这一隐患,可限于剿袭原则,也只可从与皇帝关系最近的宗室之中挑选东说念主选,如斯远在襄阳的襄藩又被东说念主总结上了,不外此次的东说念主选不是朱瞻墡本东说念主,而是其嫡宗子、襄世子朱祁镛。明代宗绝嗣,襄世子兄死弟及也无弗成。
明英宗复辟之后,给于谦、王文等景泰朝重臣按的罪名之一即是“迎立外藩”。臣子尚且因此被杀,看成被迎立对象的襄藩天然也好不到哪去,“帝颇疑瞻墡”,认为其中有襄王本东说念主的手笔。
好在后来明英宗在查询早年意外间找到了两份波及襄王的奏疏:其一即是前文说起的立朱见深为帝,零郕王监国,设法迎回留学生同学;其二为留学生自瓦剌归来后,朱瞻墡上疏敢言“景帝宜迟早省膳问安,率群臣朔望见,无忘恭顺”。
这一发现零明英宗大为漂泊,加之急需缔造典型,为我方挽尊,于是乎对襄王的格调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。
天顺元年(1457年)三月十三日,因册立皇太子及封爵诸子,给诸王致信,其中当来少不了襄王的一份。可在此除外,明英宗又单独给五叔去信,盛赞“叔父之心,即周公之心,而此二章,亦即金縢之书之比也。”同期对朱瞻墡奏请赴京朝觐之事作念出批示,暗示“本不敢烦远来,第念先帝同气嫡亲惟叔父,宗室至贤亦惟叔父。于情于谊,弗成不重欲得一见,以笃亲亲”。
此举算是开了自宣德朝以来的先河(此前为奔丧,性质稍有不同)。四月二十一日,襄王朱瞻墡抵京,皇帝陛下赐与了高大的迎接。
为洗脱嫌疑,朱瞻墡在此历程中作念了一件令后世颇为不齿之事:奏请谗谄明代宗寿陵。此举正挠到了明英宗的痒处,令其龙颜大悦,顺水推船的下令毁陵。
而叔侄之间的矛盾也因此治丝而棼。皇帝赐与的呈文亦然极端丰厚,暗示“襄王宗室嫡亲,贤德可重,特与设护卫,以表朕褒进之意”。
明初藩王肩负“藩屏帝室”和坐镇方位的重负,故各藩坐拥由精锐士卒组成的三护卫。可跟着洪武期间的逝去,削藩成为主流,永乐年间建立常山三护卫和汉府三护卫,成为藩王护卫开导的绝唱。而后诸王就藩再无护卫。
襄王府绿影壁

没成想数十年后,明英宗为酬金五叔,又特许襄藩领有护卫。天然襄藩护卫的鸿沟,比不上太族系、太宗系藩王所领有的护卫。襄藩护卫名为襄阳护卫,下辖三个千户所:本藩群牧所为中千户所,改襄阳卫左所为左千户所,安陆卫右所为右千户所。
因为属于特恩,故襄藩永乐以后唯独一个取得护卫的藩国,这一盛誉也足以让襄藩顾盼诸藩了。
而后,明英宗与朱瞻墡这对叔侄互动极多。
比如天顺元年十一月,明英宗复辟后的第一个万寿圣节,襄王派东说念主施助玲珑碧玉带看成贺礼。天顺二岁首,明英宗偶尔伤风兼以足气举发保重旬余,襄王派仪宾刘隆驰问,并送上保爱之方。后来因方子灵验,明英宗接连向皇叔求取药方,并于天顺三年九月给朱瞻墡送去珍珠、片脑、犀千里等名贵药材九百八十余斤。你没看错单元是“斤”,不是“两”。
天顺四年(1460年)四月初六,朱瞻墡再次赴京朝觐。因此时襄王殿下年已五十有五,早已超出《皇明祖训》之端正,推测这是叔侄俩这辈子最后一次重逢,故当月二十九日辞陛回国之时,还演出了一降悲欢聚散的苦情戏。
“乙亥,襄王瞻墡辞,上亲送至午门外,捏手泣别。王拜,上亦拜。王起,行数步,顾且拜,上使寺东说念主扶掖之。王起行顾且拜者,十数次。上目送出端门,乃还。百官送至端门外。见礼毕,王乃去。是行也,其赐予尤极厚云。”(《明英宗实录》)
有感于此,明英宗赐予襄藩方面三大宽宏:
其一,命户部每年从两淮运司遣东说念主用官舟载白盐三百引,送往襄藩供其食用。透澈惩处了因王府需从手上买盐,甚至食盐品性欠安,“味苦不胜”的问题。
其二,因襄世子妃李氏多病无嗣,封爵世子朱祁镛的庶宗子朱见淑为襄世孙,并赐予郡皇冠服。这是一项闻所不闻的优待。
其三,特许襄王父子每年可不经奏报,自行出门游玩数次,其中襄王可出城游赏得次数达三、五次之多。单凭这一项,就足以让那群连想要出城祭扫先王都得求爷爷告奶奶的宗王们,贵重忌妒到眼冒绿光。
后来朱瞻墡再无赴京朝觐之举,然则叔侄俩的厚谊依然在持续,襄王屡次供献药方,皇帝则屡屡进行犒赏,但有所请无有不从。
天顺八年(1464年)正月十七日,明英宗驾崩,正值的是这一日历恰与夺门之变疏导。当场皇太子朱见深继位。当年五月,襄王殿下以宗室元老的身份上疏,恳请皇帝早行婚典。明宪宗复书感谢,暗示会罢免先帝遗命扩展。
“甲戌,襄王瞻墡奏:‘大行皇帝遗诏内言嗣君以剿袭为重,婚典不宜逾期百日外……臣想四月二十七日己及百日之期,有司虽请行大礼,犹恐皇上哀慕之中,未忍举行……臣忝宗室遗老,遮拦难过。并进玉斝,以备礼筵之用。’诏曰:‘王为国度嫡亲,劝朕早行婚典,以遵遗命为孝。宜从所请,还写书报王。’”(《明宪宗实录》)
明宪宗剧照

明宪宗因少小的遇到,对待宗室比乃父要和气的多,对襄藩也多有犒赏。比如成化十年(1474年)五月,以湖广襄阳县闲田三十顷给襄府。成化十一年十一月,因襄世子妃李氏逝世,明宪宗又从南漳县划出无税地四顷赐之,充任祭田。
虽如斯,但坐龙椅的毕竟由侄子变为了侄孙,关系隔了一重,而且天顺末年,皇后与贵妃之争中还插了一脚(对德王朱见潾出阁具书庆贺,并赐之礼物兼示诲言),若干令新皇有所不喜,两边关系再无当年那么亲密。
明英宗赐与襄藩的三大特权中有一项为:襄王父子不错不经奏请自行出游。天然襄藩诸东说念主很有心中迥殊,只是偶以凶事出郭,并莫得仗着特权鼎力出城,可依然令以打压宗室为己任的文吏们特别不爽。成化初年,在负责抚治荆襄的巡抚都御史王恕建言下,这项特权被收回。是故,成化三年(1467年)其第三子枣阳王朱祁钲为出城给生母送葬,先向朝廷打了讲述。
一次如斯也就算了,可次次如斯,襄王殿下终于受不清醒。成化十二年(1476年),朱瞻墡为此上疏朝廷,搬出英庙敕书,抒发热烈起火,条款规守旧制。对此,礼部格调顽强,暗示仅有襄王本东说念主不错享有这一特权,世子和郡王不在其内。最终,明宪宗取其中,准许几位堂叔每年春秋两季各出城一次,当必须当日往还。
阿越说
成化十四年(1478年)正月十六日,襄王朱瞻墡薨逝,在位55年,享年73岁,朝廷赐谥曰宪。关于这位襄宪王殿下,汗青赐与的盖棺定论中,评价极高:
“王于诸王中为最亲,故朝廷是以眷爱之者为最优。王提神清慎,笃于贡献,尤为诚孝昭皇后所钟爱。然能守礼制,远嫌疑。故虽有异议,不为高下所疑。卒能安荣寿考,以终其天年。”(《明宪宗实录》)
关于襄王之贤,实录只说起部分,事实上他在恪守礼制、提神清慎、笃于贡献以保禄位的同期,也施恩于下,惠及藩地匹夫。
从天顺年间,明英宗赐予襄宪王的几封书信不雅之,朱瞻墡本东说念主精于医术,虽没能如叔祖周定王朱橚那般编撰出《救荒本草》、《普济方》等医学类文籍,名传千古,可对襄阳当地医学的发展也多有贡献。
襄阳城位于汉江之畔,虽在临江一侧筑有老龙堤等防护工程,可年久失修,在江水的冲刷下已渐坍决,对城池及城中匹夫组成要害恐吓。天顺七年(1463年)五月,在朱瞻墡的奏请下,朝廷下令重修江防工程。
“壬辰……襄王瞻墡奏:‘襄阳城逼汉江,自昔有堤号曰老龙,环护城郭,岁久为水冲激已渐坍决。及城南有救生桥,水大东说念主可度桥登山,以免水灾,今亦损坏。非大起工匠修筑,不足捍灾御患。请敕隔邻府州县,并本处有司军卫为之。’事下巡抚湖广左佥都御史王俭核实。俭以为宜。上命俭督有司修筑。”(《明英宗实录》)
当年的荆襄山区:十堰

今湖北十堰市,在古代被称为荆襄山区,是位于湖广、河南、陕西和四川交壤处的四无论地区,山高林密自来是流民积贮之地,自元代起该处流民问题困扰两进取百年。成化元年,河南商水东说念主刘通在荆襄一带起兵反明,自称汉王,改元德胜,此即惊怖六合的荆襄流民举义。
当年十二月,朝廷命抚宁伯朱永佩靖虏将军印充总兵官,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,统治京营及山东放工官军一万五千东说念主南下诛讨“荆襄反贼”。
荆襄山区离襄王的封国襄阳府近在目前,处于对自己抚慰的考量,朱瞻墡对对贼情一直极端夺目,据说朝廷雄兵南下,特地派东说念主将一封谍报送到白圭案头。天然表错了情,但起码阐扬了他的材干及对方位的关注之情。